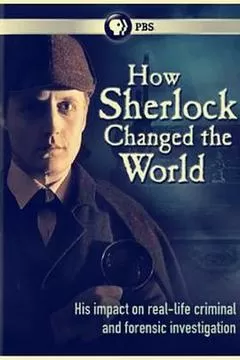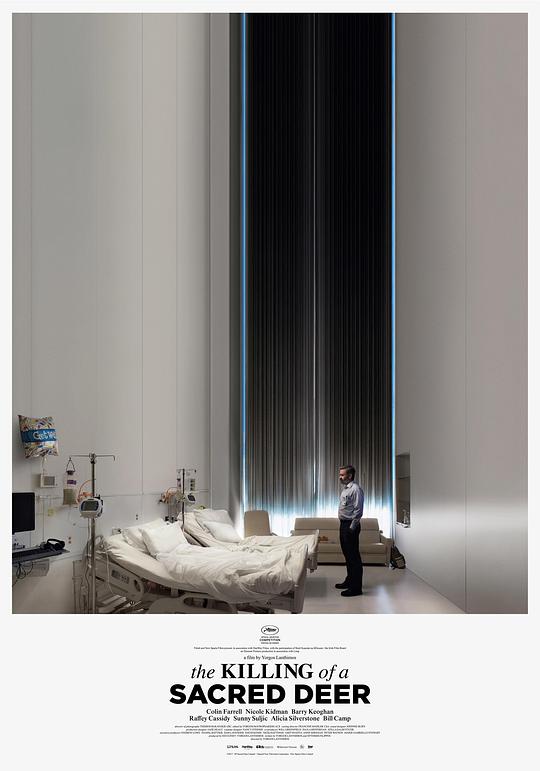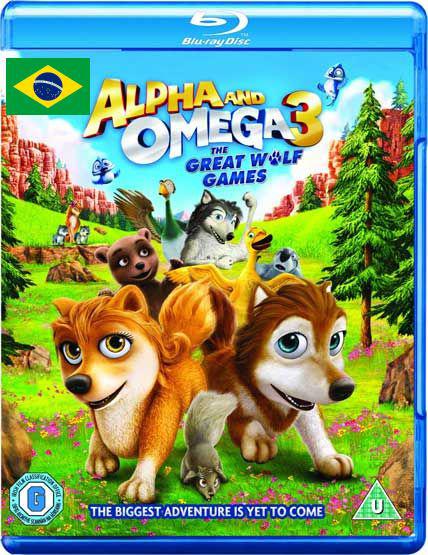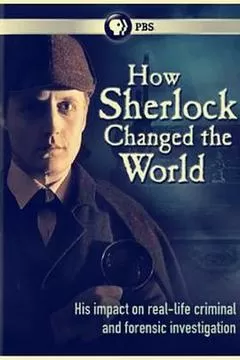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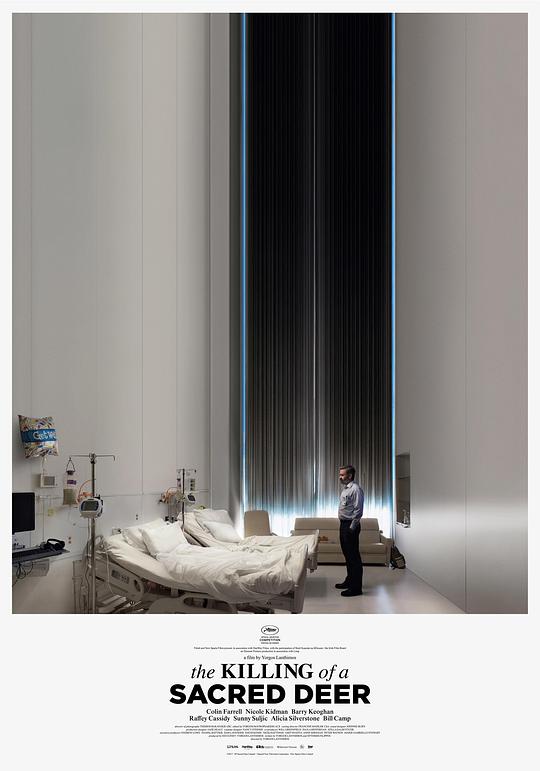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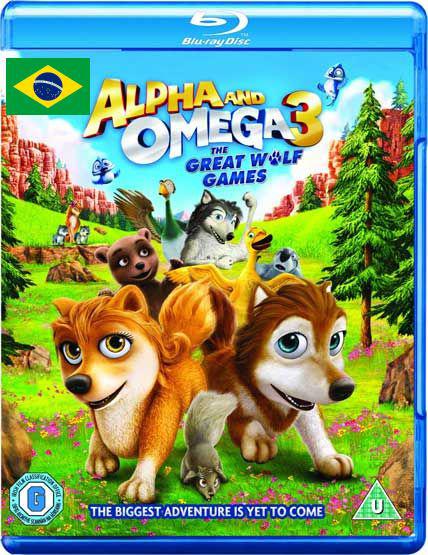

毕赣的新片《狂野时代》上映已一月有余,至今在公众号等领域仍不断有评论问世。
这是非常少见的。首先作为一部显而易见的文艺片(艺术片),它的受众群体是非常小的,即便是因为有流量明星易烊千玺的粉丝加持的情况下,《狂野时代》的票房也仅仅达到两亿,也就是说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实际是很少的。
然而,这部影片在社交媒体上的声量与其票房完全不成正比。以猫眼数据为例, 《狂野时代》票房不到2亿,累计观影人次540万人,除去一些粉丝包场之类的,实际观看人次还要更低。
然而,这部影片的营销传播人次却达到将近87亿,与之对比,年末的大热影片《疯狂动物城2》的票房已经40亿,观影人次1亿人,而营销传播人次才220亿!
所以,《狂野时代》是那种非常特别的,看的人少,讨论的人却特别多的“话题电影”。
评价就更是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状况。普通的电影观众大多觉得“不好看”,冗长,乏味,更多表达“看不懂”;而我所知道的影视从业者、创作者几乎大多都很喜欢《狂野时代》。
这充分说明《狂野时代》确实是值得拿出来深度分析讨论的作品。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针见血的关于《狂野时代》的评论,即便是那些喜欢这部电影的,所说的也大多是表现手法,影像风格等等,就是没有人直截了当的说出“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什么”?
这倒也不意外,毕竟毕赣自从以《路边野餐》声誉鹊起之后,他的作品就一直引发争议。毕赣也一直是媒体圈和文娱圈的宠儿,虽然他的几部片子看上去都是不怎么赚钱的(《地球》可能赚钱了但被骂惨了),但毕赣却一直不缺媒体资源和关注。
所以评价毕赣和《狂野时代》是个不太容易的任务,但问题终究是要解决的。
隐喻?NO!
首先,在分析《狂野时代》之前,我们要先明确一点,即摒弃那种“这部影片是在隐喻某某历史”的思维。
这种姜文式的解读在2025年的今天,事实上已经遭到很多观众的厌弃,虽然它在2010年《让子弹飞》上映后不胫而走,甚至被认为是某种“高级”的表达和解读方式;但今年夏天姜文的新作《你行!你上!》遭遇票房惨败,已经充分说明了观众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审美疲劳。
对于这一点,我个人的观点是,如果你真的认为某部影片在隐喻什么历史,那我建议你直接去看历史书。无论什么电影,无论表达的技巧多么高妙,它都不可能比历史书籍让你对真正的历史更了解。
当然,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环境中,经常有些“不可言说”之处。但我必须指出的是,电影这方面相关的禁忌比书籍还是要更严格。也就是说从表达的限制来看,其实电影本身就不适合表达历史的深度细节。
所以我看到那些“《狂野时代》隐喻了中国某某历史”的评论,尤其是言语之间还经常遮遮掩掩故作神秘感的,都是直接略过。还是那句话,建议你去看书。
你行你上
那有人要说了,既然你不喜欢从电影中去解读历史,那么《狂野时代》肉眼可见的分段式结构,每段体现一个历史时期,这还不是跟历史有关吗?
说到这一点,我们又要回到毕赣本人身上。
正好在《狂野时代》上映期间,罗永浩的播客节目《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又上线了毕赣的长篇访谈。
我看过毕赣不少访谈,罗永浩的访谈虽然时间很长,但总体上,并没有提供特别多新的信息,反而看完后更加坚定了我对毕赣的已有印象。
这不代表我对毕赣有什么“成见”,只是毕赣作为一位青年导演,他的成长轨迹基本都在信息和科技发达的时代,因此缺失某些关键点而让电影解读出现致命盲点的可能性不大。
毕赣生于1989年,勉强也可以算90后的一员。既然谈到代际,那就不可能有非常严格的划分,所以毕赣身上有很多90后的特质也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
并且,他在当年《十三邀》中说出的那句“不顺从,不反抗”至今是我认为对90后的最好精神总结。
如果说到导演群体,我之前已经总结过这些年风生水起、已经成为电影圈中流砥柱的“80后导演群体”,比如郭帆、文牧野、饺子、贾玲、饶晓志、申奥、韩延、戴墨、苏伦、忻钰坤等等,其中79年11月出生的路阳,风格其实也可以归入“80后导演”;以及不幸身故的胡波等。
而毕赣虽然是89年的,但他的风格跟前面这些导演相差甚大,反而可以跟后续的“90后导演”视作一个群落。
目前比较有名的90后导演,大概就是邵艺辉,魏书钧两位。另外还有一个演员转战导演赛道的李鸿其。
我们在提到90后,包括近年更多被提起的一个概念:Z世代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不能忽视的。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第一次遇到了“间接经验大过直接经验”的情况。
90后整体成长在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他们可以用便捷的方式接触更多“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相对于80、70、60等前辈来说不可比拟的优势。
然而同时,这种间接经验大过直接经验造成的结果,是90后的精神世界更多体现出了“独乐乐”和同质化倾向。独乐乐是因为娱乐方式的极度便捷,毕竟一个手机在手就能刷一天,饿了可以点外卖,完全不需要去接触“真实的世界”;同质化是因为内容的生产在大数据和算法技术的不断优化下,精准投喂,使得更多的人处于“信息茧房”。
当然,这么说很多90后肯定是不服气的,反而会觉得前面代际的人从小没有这些信息技术的加持,从而信息闭塞,视野狭窄。
这种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孰短孰长的争论,可能一时半会儿很难下结论。但我想说的是,这种状况显然影响到了90后导演的创作。
就以魏书钧为例,他到目前为止的四部长片:《野马分鬃》《永安镇故事集》《河边的错误》《阳光俱乐部》,其中三部都是元电影叙事,或高度包含“迷影情结”。哪怕是聚焦残障人士的《阳光俱乐部》也充满了迷影情结(不仅仅是贾樟柯的客串)。
一个导演的创作风格如此同质化,且似乎除了“拍电影那点事儿”就没有其他感兴趣的事儿了,那怎么能不让人感觉到乏味和单调呢?
另一边的邵艺辉也有类似的问题,她的灵气和个人的生活积累似乎在成名作《爱情神话》中全都消耗了,《好东西》风格的悬浮和内容的苍白与《爱情神话》相比是一目了然的,甚至都不像一个人的作品。
另一位李鸿其,虽然其导演处女作《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宝贝》还未公映,但从内容看,讲的也是他自己做剧团的故事。
总体上讲,90后导演创作者似乎缺乏对自己生活范围以外的人和事的兴趣,这是比信息获取范围更加要紧的事情。
而89年的毕赣也同样体现出类似的问题。《路边野餐》讲的是他生活的凯里小镇的故事且不论,《地球最后的夜晚》就是用更充足的资金和配置把《路边野餐》重新拍了一遍;而《狂野时代》更是直接聚焦百年电影史,真的让人对中国的90后创作者有此疑问:你们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其他感兴趣的东西么?
迷影
但要这么说,似乎又有一种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耳提面命的“爹味感”,尤其是八零后当初也是被人提着耳朵这么过来的。我觉得有迷影情结没什么问题,关注自己也没有大问题。
而毕赣在这一点上表现的更为极致,正如我的标题所说,《狂野时代》是一部“零信息”电影,这才是他有别于其他任何导演的地方。
其他导演,哪怕是我之前所说的几位90后导演,虽然技巧有别,视野和阅历也有各人的局限,但他们仍然是有表达的。魏书钧可能对自己所处的圈子的各种尴尬和荒谬的乱象欲说还休,而邵艺辉可能对当代年轻女性夹在事业和爱情、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窘迫处境欲罢不能。
而毕赣似乎就真的没有什么表达欲。《狂野时代》是这样一种电影,就是你看完之后,不会对这个世界和导演本人增加任何信息。
简单说,如果我看了其他导演的电影,可能会对世界上的某个人某件事增加某种认知,比如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那件事是那么发生的。这是一种“正信息”。
也有可能会减少你的信息,即打破你原有的认知,却又没有新的东西,比如一般世俗观点认为某件事是这么发生的,你看完这个电影后发现自己搞不清楚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了,这就是“负信息”。
而《狂野时代》就真的是“零信息”,你看完后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电影本身,甚至是对导演的内心世界都不会增加任何认知。
没错,你可能会从中看出导演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对影像语言的热爱,可问题它不是信息啊,就算这带有导演的个人特质,它也早就体现在毕赣的前作《野餐》《地球》中了,《狂野时代》不能告诉你任何你之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当然,提供认知并不是电影必须的要素。但作为对现实世界和内心世界的反应,电影必然带有现实的各种“毛刺”、褶皱和突兀,这些东西哪怕不是创作者主要表达的内容,它也依然会从光影的缝隙之间漏出来。
而毕赣却真的把《狂野时代》打造成了一个完全不带有信息含量的东西,基于这一点,我甚至很难说它是一个“作品”,因为它完全回避了文艺创作的社会功能,而个人性也没有超出已有作品所表达的范围。
那么问题就回到了,为什么毕赣要这么做?
代际
这还是要回到毕赣当年在《十三邀》中的那句“不顺从,不反抗”上。
我们知道,许知远作为一个大龄文艺青年,这些年一直在“愣头青”式地对这个时代的消费主义特质和庸常的内容空间做着各式“反抗”,甚至最近他与毛尖在公开场合的龃龉也成了一时热门话题。
而毕赣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创作者(《地球》上映的时候不到三十岁)却早早进入了“不顺从、不反抗”的状态,他到底是怎么看待、怎么处理自己与这个世界,包括他的作品的关系呢?
让我们回到影片的第一部分。我相信熟悉建政的人看到舒淇饰演的“大她者”时都会会心一笑。
在中国目前的表达环境中,“不可言说”是不会被主动提及,但无处不在的一个点。因此,如果毕赣在《狂野时代》中设置了“大她者”这一角色是为了隐喻什么的话,那自然是可以说得通。从舒淇这个角色在一头一尾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也能感受到这样设置的用意。
如果这样来解释,我们倒是可以迅速理解《狂野时代》为什么是一部“零信息”电影,因为“零信息”是最安全的。因为表达的前提就是信息,如果连表达信息的欲望都没有,那么自然是绝对安全的。
这似乎也能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建国后不许成精”的不成文规定下,影片倒数第二段中竟然还会出现黄觉和李庚希饰演的吸血鬼形象。在当下愈发严苛的审核规定下,你是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的。
而这是否就是全部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间的几段似乎都是些来填充时间的“废戏”了。
这显然不能让人满意,不能让人接受毕赣花了如此大的投资、2小时40分的时间(与《霸王别姬》长度相同)只是为了给观众和审查者搞一次行为艺术。
答案还是藏在毕赣的成长经历和他的既有作品中。
毕赣在《十三邀》以及“罗永浩的十字路口”访谈中,都谈到了年幼时父母带他去看电影的经历。后来父母离异,每次看完电影后走出影院,走到一个广告牌时就停住了,父母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走。他在描述这段记忆时,非常有画面感。
当然,如果就此分析下去,我们只会得到一个童年创伤式的非常心理学的版本。
在《十三邀》中,毕赣的小姑父陈永忠还提到,自从他拍了电影后,女儿愿意和他说话了。在这件事上他很感谢毕赣。
拍电影可以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毕赣来说,是一种“意外之喜”。当然还不止于此。
毕赣在《十三邀》访谈中,还谈到了他们这一代人,说自己“涉世未深,却又提前衰老”,又说“我不想把他们想得那么肤浅,”“我们这代人是被诋毁最深的一代人。”
这些看似矛盾的语句交织在一起,加上那句“不顺从,不反抗”,构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
过去我认为九零后大多只爱关注自己,不愿意以代际来发声。最近发现,还是有的,比如以某篇文章震惊全网的某李姓投资人。
最近看到90后企业家、影石科技创始人刘靖康登上“罗永浩的十字路口”,又有了一些启发。访谈中,他在谈到因为进入无人机全景摄影市场不可避免的与这方面的霸主大疆展开正面对决的时候,反复强调“我们对大疆非常的respect”。
这形成一种非常有趣的张力。我们不能忘记,90后第一个闻名全国的创业者是OFO的戴威,他与80后的胡玮炜创立的摩拜也曾经是针尖对麦芒的对手。最终,年轻气盛的戴威并没有笑到最后,还被70后的马化腾评价失败的原因是过度依赖个人控制权。
可见,无论是学习生活还是事业,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总是成为90后的核心问题,而影石刘靖康的表现显然比他的前辈要成熟不少。
这让我回想到毕赣。早已树立了“不顺从,不反抗”原则的他,加上“地球”营销事件的洗礼,理应对个人事业的发展和与外界的关系有更成熟的思考与态度。
而《狂野时代》也许就是处理他与电影、与外界、与自我关系的另一种方式。唯有回到“零信息”的状态,才可能最大程度的排除一切干扰,回到本源,也才有可能最大幅度地链接所有的个体,尤其是相邻代际的人。
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
解决艺术的永恒性秘密的钥匙究竟在哪里呢?一方面,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新作,……从而另一方面,这里反而产生继承性、统一性的问题。……人类的心理结构是否正是一种历史积淀的产物呢?也许正是它蕴藏了艺术作品的永恒性的秘密?也许,应该倒过来,艺术作品的永恒性蕴藏了也提供着人类心理共同结构的秘密?……
随笔礼记,历史巡礼,对于领会和把握这个巨大而重要的成果,该不只是一件闲情逸致或毫无意义的事情吧?
俱往矣。然而,美的历程却是指向未来的。